https://news.creaders.net/china/2023/08/17/2638239.html
我前两天刚刚吐槽过
“上海外滩夜景各种装饰灯光、跑马灯,一种浓浓的乡镇味道。本人认为:作为国际知名城市,全世界人都知道上海,但上海的夜景灯光越发花里胡哨,没有一流城市的格调。”

最近,网友给上海市政府官网信箱的留言引发了热议,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:虽然也有人觉得“这些灯光是我们的特色”,但更多人早就觉得,这些眼花缭乱的灯光并不好看。夜景一言难尽的又何止上海?更进一步说,为什么国内城市的夜景都长得差不多,而且如此缺乏美感?
城市的美感,绝非可有可无
虽然这次上海的夜景遭到吐槽,但从全国来看,上海在这方面已经是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了。上海之所以被吐槽,恰恰是因为市民的审美眼光更挑剔。
4年前,照明设计师齐洪海在“一席”的一场主题演讲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“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状况是,没几栋楼好看,没几栋楼真值得被照成什么样”,横向比较来看,问题倒是“为什么上海做得比较好?”
上海夜景如今竟会被视为“乡镇土鳖风格”,想当初,夜上海可是无数国人的现代性体验。上海是第一个安装路灯的城市(1879年),比号称“光之城”的巴黎只晚了4年,比纽约都早了2年,更比成都(1902年)、北京(1904年)早了能有一代人的时间。不夸张地说,上海的路灯照明系统,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现代意义上的“夜景”。

1981版电影《子夜》剧照。
以1930年的上海滩为背景的小说《子夜》中,从闭塞的乡下来的吴老太爷被儿子吴荪甫接到上海,受大都市街头车辆排山倒海的速度惊吓,又被车里车外应接不暇的璀璨霓虹刺激,无法承受这极致的反差,最终晕厥乃至暴毙。
我们现在已经对都市夜生活里密集的声光电习以为常,很难体会那种冲击了。国内城市里缺少设计感很好的各种印刷海报,却到处都能看到各种电子屏,在拥抱新事物方面,我们更为热切而不加节制,甚至到了“技术滥用”的程度。
常有人嘲讽,一些大城市即便人口达到了数百万人,也只是“大一号的县城”,也许砸了更多钱,但在审美上和县城没有本质区别,因为这些城市的景观设计,考虑的重点就不是“美”本身,而是一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。但这就像当年英国作家萧伯纳第一次在纽约看到百老汇和第42街的霓虹灯时的嘲讽:“如果你不识字,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。”

百老汇大道夜景/@Denys Nevozhai
确实,美国也曾被欧洲人嘲讽为“没品位”,乔尔·科特金在《新地理: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》一书中还承认:“‘品位’的培养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,被广泛认为不是一种主要的价值。”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“没文化”,还因为在一个更平民化、更务实的社会中,这种往往与文化身份地位绑定的审美品位(taste),对人们来说用处不大,似乎没必要那么讲究。
美学的判断(“没品位”)只有在一个看重文化身份的知识主义时代才有可能,而在价值观更传统的社会里,评判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——想想看,现在很多人看到女孩子打扮新潮,还会说“妖艳”,意思是说,虽然美,但不道德。既然如此,那么单纯的“美”没有意义,它首先必须考虑的是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和地位展示。
不仅如此,我们还常常觉得,纯粹的审美应当屈从于生存需求——“饭都吃不饱,还谈什么品位?”在我乡下老家,“有吃无看头”是一句褒奖,从物品到人都可以这么形容,意思是“虽然样子不咋样,但很实在”;反过来,“绣花枕头”则是众所周知的贬称。这足可看出,在实用主义的人眼里,美感只是次要的表象,远不如实用性重要,但就像阿兰·德波顿在《幸福的建筑》中指出的,“伟大建筑的本质就在于那些在功能上并无必要的元素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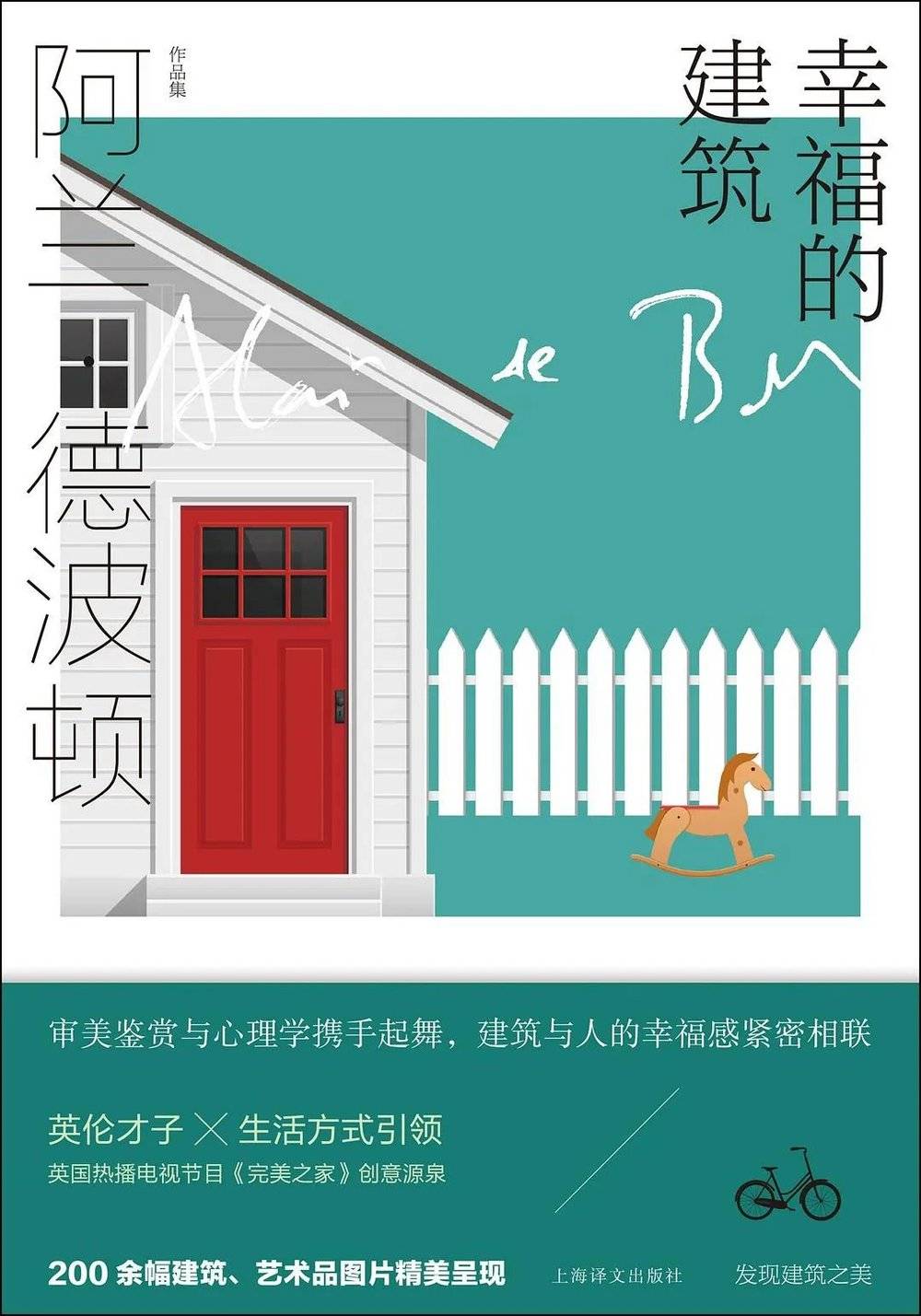
《幸福的建筑》
[英] 阿兰·德波顿 著 冯涛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-7
100年前的1922年,梁启超应邀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演讲《美术与生活》,痛切地说:“中国向来非不讲美术——而且还有很好的美术,但据多数人见解,总以为美术是一种奢侈品,从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样看待,认为是生活必需品之一。我觉得中国人生活之不能向上,大半由此。”
我们的审美之所以匮乏,另一大原因是:内向、关注家园的中国人,向来就只关心自己的小家,传统中国城镇原本就缺乏像古希腊、古罗马城邦那样大型的公共建筑,也不像他们那样把街道、广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芦原义信曾在《街道的美学》一书中说,日本住宅的基本思想过分注重在家的内部建立起井然的秩序,把“内眺景观”或者说把内部空间秩序放在首位,却不在意作为外观的街道美学,造成了作为城市景观来说极为贫乏的街道。
现在,吐槽上海的夜景灯光竟然成了一个热议话题,这本身也说明,至少有一些人开始注意到,城市并不只是我们居住在其中的实用生活空间,美感也绝非可有可无。有争议,意味着这个问题终于引发公众关注了,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:怎么做呢?
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审美?
审美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,对于什么才是“美”,不同的人常常有着相去甚远的看法。老话说的“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”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都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:“美”多少都带有一点主观性,你觉得美的,别人未必也这么看。所以法国作家司汤达早就感叹过:“有多少种幸福观,就有多少种美。”
即便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些城市地标的景观,当年也都曾充满争议。美国波特兰市政厅现在被普遍看作是北美第一座后现代主义建筑,但建筑师迈克尔·格雷夫斯(Michael Graves)当初的设计太超前,市民很难接受其审美,不仅没有将其视为骄傲,倒是一度相当反感。
悉尼歌剧院如今早就被视为悉尼这座城市乃至澳大利亚的标志,但在它漫长的建造过程中,争议几乎从未平息。无数人抱怨这一设计华而不实,导致预算严重超支,加上丹麦设计师伍重决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标准,结果是迟迟未能完工。然而现在人们大多已经淡忘了这段往事,任何到此一游的来客,如果不在那个大贝壳前留影,简直感觉好像没去过悉尼一样。

曾饱受批评的悉尼歌剧院静静地伫立在岸边 / @photoholgic
更著名的是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。1889年它落成时,激起了海啸般的争议,很多人批评这座工业风的铁塔毫无美感,艺术评论家约里斯-卡尔·于斯曼蔑称它是“伸开双腿的妓女”;画家乔治·瑟拉却十分喜欢;至于作家莫泊桑则尖刻地嘲讽,说他喜欢在埃菲尔铁塔上吃早餐,因为那是整个巴黎唯一看不见这座碍眼的铁塔的地方。
1977年,蓬皮杜艺术中心落成,再度在巴黎投下震撼弹,无数文化人都抨击它简直是太丑了,甚至“完工后仍然像未完工一样”。芦原义信对此有一段巧妙的双重嘲讽:“它在巴黎石结构建筑的整齐稳重气氛中,怎么说也是不协调的。如果它是建在东京的繁华街道中,恐怕只会被误认为是仓库或工厂,而不会引人注目。因为日本城市的街道太杂乱了,再怪的建筑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”
回头看这些艺术史上的潮起潮落,有时可能让人非常困惑:究竟如何分辨是“创新”还是“真丑”?标准到底在哪里,又该由谁来说了算?

蓬皮杜艺术中心 / @Meizhi Lang
在那些成功的案例中,很突出的一点是:虽然当时引发巨大争议,但最终那些专业人士的创新经受住了考验,并以其前瞻性革新了时代的审美潮流。相比起来,现在国内各地城市景观的问题,乍看是“美丑”的审美趣味不同,但更往里一层说,是专业人员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的体现。
照明设计师齐洪海说,国内许多城市夜景灯光都是“高亮度比、片段化”的,投资巨大却缺乏美感,人眼看着既不舒服,也难以捕捉到丰富的层次感,因为“不是光线越多,看到的就越多”。就算是一些做出来还不错的,但一场城市改造,就推倒重来了,他无奈地说:“照明是个很幻灭的事,说没就没了。”
对于后发国家来说,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:从国外引入的理念和技术,是否能适应本土的文化环境?芦原义信当年虽然痛陈日本的公共景观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(直白地说就是“有钱了,城市还那么丑”),但他也强调:“西欧理性主义的观点,本来就不应该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的现有城市中。”因为由此产生的不协调又会造成新的“丑”。
这不仅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专业人员,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,还需要让社会公众也参与进来。

美丽的济南市 / @jerry she
2011年,南京曾为地铁3号线建设而试图将沿线已有百年历史的法国梧桐移栽,引发许多市民强烈不满,他们发起绿丝带活动守护,最终市政府退让,承诺市政建设“原则上工程让树,不得砍树”。但这些年的“大拆大建”浪潮中,更常见的则是原有的城市景观为新开发让路:1992年,由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·菲舍尔设计的济南老火车站灰飞烟灭,时至今日,都一直是老济南人心头的痛。
任何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,是所有市民共同创造的生活空间,在这一意义上,阿兰·德波顿说得没错:“一个国家的街道、房屋、办公楼和公园的外观,共同表现了当年设计这些建筑、如今栖身这些建筑的人的精神肖像。”地理学家皮尔士·刘易斯也说过:“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,却可触知、可看见的自传,反映出我们的趣味、我们的价值、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。”

上海夜景 / @Zhou Xian
那并不只是“美感”而已。根据现代城市规划学的理念,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,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,一个符合人类体验原则的“丰富环境”(enrich environment)不仅能带来更好的视觉感受,也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,因为几乎所有研究都证明,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审美体验是一种无声的熏陶,对于人的精神感受、心理健康乃至降低社会犯罪率,其潜移默化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。
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城市变得更美:因为那样可以使身在其中的我们,生活变得更美好。